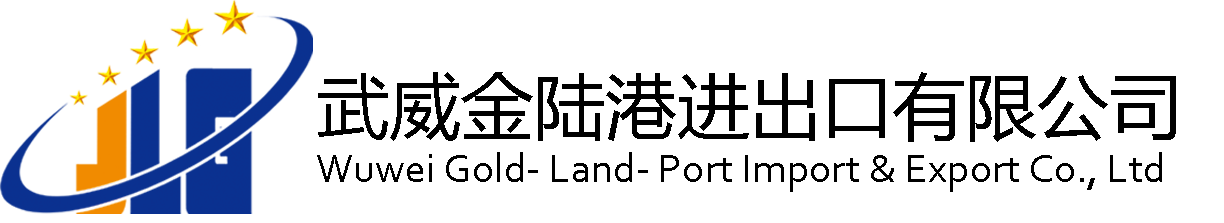近期,中国贸促会发展研究部调研小组实地走访中西部有关省区外商投资管理部门、经济开发区及外资企业,了解当前利用外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河南、新疆等中西部省区积极落实外资企业审批制改革和“放管服”改革举措,着力营造优良投资环境,并大力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及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总体呈现良好势头。受访外资企业大都表示,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外企投资准入限制日益放宽,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同时,调研小组也了解到,当前利用外资还存在三方面问题。
1利用外资平台和政策资源相对不足
近年来,国家积极鼓励引导外资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但目前部分中西部省区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吸引和利用外资平台不足。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工业园区是利用外资的重要平台。调研中,河南、新疆两地都反映,由于两省区利用外资起步较晚,其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数量远远少于沿海发达地区,这成为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一大瓶颈。河南省商务厅外商投资促进处负责人表示,河南利用外资的增量项目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但河南目前只有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用外资的规模。其他中西部省区如青海、贵州都只有2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二是现有利用外资平台发展受制约。地方外资管理部门和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区虽然已经得到一些政策倾斜,但总体上仍然面临一些发展难题。首先,部分园区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需求,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其次,部分园区发展饱和但仍有产业集聚优势,亟待破解土地制约;再次,有关部门目前对园区一些考核指标更适用于考核沿海地区的园区发展,如单位工业用地产出指标,而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园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特别是很难衡量近年来兴起的占地面积较大的国际物流园区的发展。
三是利用外资的促进体系比较薄弱。目前,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比例远远落后于同类工业园区,例如,青海某国家级开发区现有外资企业16家,仅占开发区工业企业数量的3.7%。除了硬件环境存在劣势外,部分中西部省区在利用外资的促进体系建设上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仍有不足,如新疆等省区还没有专门的外商投资促进机构。同时,在鼓励外资向中西部转移的背景下,目前缺乏支持中西部外商投资促进的专项资金安排。
2传统利用外资模式面临新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一是利用外资面临“低端产业不想要、高端产业难引进”难题。郑州经济开发区商务局负责人说,在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对引进外资的需求从中低端产业逐步转向高端产业,但引进国外高科技企业很困难,特别是面临外国政府方面的阻力。例如,该开发区曾积极引进一家美资汽车电池公司,但其因美国商务部门阻止而最终没能落地。又如,郑州一家企业近期正在收购德国博世电机的起动机与发电机业务,由于牵涉高新技术转让,此项交易不仅需要经过德国政府的安全审查,还需要经过欧盟反垄断及其他相关部门审核,困难重重。
二是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模式转型面临瓶颈。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依靠土地、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而2014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从政策层面终结了这种旧的招商引资模式。地方外资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普遍表示,按照内外资一视同仁原则,地方政府目前很难再为外资企业提供土地和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只能转向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但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部分中西部省区在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上普遍较为落后,而且前者在优化投资环境方面迈出的步伐更快,这种转向改善营商环境的招商引资新模式短期内很难增强中西部省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三是外资企业审批制改革后,事中事后监管有待完善。地方外资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外资企业设立由审批改备案后,总体上地方相关部门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有所弱化:一是难以掌握外资企业真实信息,目前未强制要求外资企业填报股份情况、实际控制人等信息,这可能会为今后了解外资企业实际渗透状况、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留下隐患;二是与外资企业的常态化联系减少,以前可以通过年检、审批等方式接触外资企业,审批制改革后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少了,也很难掌握其活动情况与意见诉求。
3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仍有进一步改进空间
调研人员在河南、新疆等地分别组织召开外资企业座谈会。从与会外资企业反映的情况看,中西部地区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以下改进空间。
一是产业集聚不够,服务配套能力较弱。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创新能力的规模企业集聚区,缺乏对外资吸引力。以甘肃为例,该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晚并且滞后,目前引入的大多数外资企业规模都较小,多从事小型加工和商贸服务,难以产生聚集效应。新疆部分外资汽车制造企业反映,由于在当地长期无法培育配套企业,该企业大部分零部件都要从上海、江苏等地采购,增加了运输和库存成本。新疆部分外资制药企业表示,本地原材料企业规模小、且不规范,该企业大量原材料需要从安徽亳州采购,成本不断上升。
二是部分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外资企业反映,目前一些地区办理证照仍存在周期长、效率低的现象。河南某外资食品企业称,国家最新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榨油从限制类行业改为允许类行业,该企业准备投资一个年产值40亿元榨油厂项目,从基建到生产只需要1年,但规划证、施工证等相关证照因涉及不同层级的管辖部门,办理时间需要半年以上,导致投产进度延误。四川部分外资企业表示,某地方政府宣布出台对所有企业实行房租优惠和税收减免举措,但在实际执行中只接受本地企业申请,而且外资企业在当地难以参加政府类项目的投标。新疆部分外资酒店服务企业反映,少数基层税务、工商部门因不了解新出台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无法为企业办理相关业务。
三是部分地方政府监管滞后导致新业态无法落地。河南某外资餐饮企业反映,该企业所属的连锁餐饮集团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流动餐车服务的新项目,由于流动餐车介于门店(工商部门负责)、小作坊(质检部门)和摊贩(城管部门)之间,三部门的监管职责划分不清,导致企业在一些城市无法办理营业执照,项目最终无法落地。新疆某外资旅游服务企业反映,该公司准备投资一个沙疗项目(注:沙疗是一种将身体置于适宜的沙子当中,集热疗、按摩等于一体的综合理疗法),由于不同部门对于该项目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关规定的理解不同,使得该项目难以落地。
四是部分外资企业负担仍然较重。尽管国家出台一系列降低企业成本的举措,但受访外资企业反映,企业税费、劳动力、环保等相关成本仍然较重。重庆部分外资企业在被问及当前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排名前5位的挑战分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税费负担过重和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其中有两项都与企业负担有关。河南部分外资房地产企业表示,一些基层税务部门不是按照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征税,而是按照财政收入增长指标征税,要求企业自查补税,然后再开展稽查,以完成征税目标。这使得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反而多交税,加重企业的负担。
 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营业执照